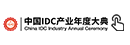中国IDC圈2月25日报道:伟大的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离开人世后,关于他的作品和苦难人生,经由无数的著述,尤其是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和由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梵高传》,而广为流传。其中关于梵高的死是这样的:“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世人普遍接受了这一戏剧性的诗意描述———一个几无容身之地的天才的悲剧,一个艺术的牺牲者的形象。
不久前,译林出版社引进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史蒂文·奈菲与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却揭开了梵高之死的罗生门———基于当今大数据技术和法医技术得出的结论,梵高不可能死于自杀!
凶手是谁?证据何在?“自杀说”的源头来自哪里?随着作者条分缕析的叙述,证据被一点点摊开———梵高死于意外的他杀,他用“自杀说”保护了真正的凶手,也用“自杀说”坦然地迎向死亡。
———编 者
没有任何物证,只有梵高的自述
1890年7月27日午后,巴黎以北20英里的奥威尔镇,梵高走出他借居的拉乌尔旅店,随身带着他的画架、画布、颜料、画笔、素描本,镇上的人们已经对此情景习以为常。然而太阳刚刚落山,正在旅店晚餐的人看见他空手回来,“手捂着腹部,走路似乎一瘸一拐”,其中一人回忆道,“梵高的外套纽扣都紧紧扣着”,在炎热的傍晚这样看上去特别古怪。梵高跌跌撞撞爬上阁楼他那间7个平米的房间。旅店老板拉乌闻讯赶紧上楼到梵高的房间里,发现他正蜷缩在床上,梵高掀起衬衫,给拉乌看了看自己肋骨下的一个小弹孔,说“我弄伤了自己”。两天后的29日深夜,他对从巴黎赶来看护他的弟弟提奥说:“我想就这样死去”,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30日,他被安葬在奥威尔镇外的麦田里,年仅37岁。
尽管有2个目击者在事件发生当晚看到梵高走在僻静的通往夏彭瓦尔村的路上,那条路是两旁带着围墙的农场,与麦田方向相反 (麦田在小镇的另一头,从麦田到拉乌尔旅店所经之处是热闹的公共街道),但警察还是按照梵高的自述,搜查了麦田,一无所获,连血迹都没有。
当时也有目击者说,梵高对自杀行为的“忏悔”言不由衷,躲躲闪闪,警方直接询问他:“你是不是想要自杀?”,他不太确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当别人告诉他企图自杀是一种罪行时,他似乎更关心其他人会不会被问责,而不是他自己是否会被定罪,他说:“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要自杀的。”
很快,那些知道梵高曾暂住精神病院和那些见过他的畸形耳朵的人将梵高的自残行为和自杀行为联系起来。人们越来越怀疑他死于自杀。
7月30日,评论家埃米尔·贝尔纳来到奥威尔参加梵高的葬礼,他写了一封信给批评家艾尔贝·奥里耶,信中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戏剧化地讲述了事件———“周日晚梵高走进奥威尔的乡间,他把画架倚在干草堆上,然后走到别墅后面拿一把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他说消息来自镇上人的叙述。
从那时到现在,枪击发生的地点从来没有被最终确认过———警方没有找到那把致命的手枪和弹壳,没有找到梵高出门时携带的任何东西,没有进行过尸检,那颗致命的子弹没有被取出来……虽然当时医生就认为子弹是从距离身体较远的地方、而且是以一个倾斜的角度射入的,这不是一个自杀者能做到的。
梵高“自杀”后没有留下遗书,弟弟提奥在枪击发生后的数天内,整理梵高房间和画室时,并没有发现任何“道别”痕迹。
那把致命手枪的主人是16岁的少年
梵高死后66年的1956年,也就是好莱坞电影 《梵高传》 上映之后,82岁的法国人雷内·萨克里顿站了出来,不同于许多其他证人,雷内是在梵高死后并成名很久之后,才第一次作出陈述。梵高死的时候,他16岁,是巴黎最著名的公德赛中学学生。身为有钱药剂师的儿子,他和哥哥加斯顿每年夏天都会到奥威尔镇的瓦兹河畔,在父亲的别墅旁垂钓打猎。比起雷内的好动,18岁的加斯顿更喜欢艺术和音乐。通过加斯顿,雷内认识了画家文森特·梵高。
当雷内不和哥哥在一起时,他会和另一群喜爱吵闹的男孩厮混,狩猎探险。雷内从巴黎带了套牛仔服,并为这身衣服搭配真枪———那是一把老式380口径手枪,有些散架,但还是能够射击,他一般都放在自己的帆布背包里。据雷内所说,这把枪是旅店老板古斯塔夫·拉乌卖给他的。
奥威尔是一座小镇,在法国乡间左轮手枪还是件稀奇物,不过,拉乌的生活十分公开,雷内又喜欢带着枪到处炫耀,两人的许多朋友对这位旅店店主的罕见武器很熟悉。在镇上,雷内和他的追随者们没事就消磨时光,比如捉弄荷兰人梵高。这群“熊孩子”把盐放在他的咖啡里,然后在远处看着他一边吐咖啡一边生气咒骂;有时把一条蛇放在颜料盒里,当梵高发现蛇时,几乎要晕过去。雷内注意到,梵高沉思时会舔画笔,就趁他不注意,用红辣椒擦拭笔头。雷内承认,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使文森特发狂”。
虽然梵高避免和雷内那伙人接触,但他从不抱怨,甚至脾气很好,这从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也能得到佐证,信件中从没提及被戏弄。梵高屡屡原谅恶作剧的雷内,部分原因是他想与加斯顿保持难得的交情,据雷内所说,梵高认为加斯顿在绘画方面的想法挺超前。当然,他也很感激加斯顿常为他支付酒吧账单。雷内还有一个筹码,他发现,当梵高看到那些来自巴黎的餐厅女郎时,他的目光充满渴望,想要把梵高逼疯变得越发容易。雷内回忆道,他经常刻意激起文森特的怒火来戏弄他。
可以想象,冲突在那一天升级了。挑衅的熊孩子、愤怒的梵高,加上酒吧酒精的刺激,擦枪走火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检查梵高伤口的医生在报告中提到:枪击是在腹部而不是在头部;子弹以一种不一般的倾斜角度射出,而自杀时子弹通常是直射进去。此外,子弹显然是从距离梵高“很远的”地方射出,远到他本人根本无法扣动扳机。况且,如果梵高铁了心要自杀,他为何不“彻底解决自己”,反而痛苦而尴尬地走回旅店阁楼?
已经高龄的雷内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他枪击了梵高,但他的否认与接下来的叙述并不一致。比如他在受访时说自己无论去哪儿都带着他的帆布背包,后来却说直到去了诺曼底才发现包里的枪不见了;他暗示梵高在自杀当天就从他那儿把手枪偷走,这说明雷内本人当时仍在奥威尔。更多的证据则表明,最初的枪声过后,闯祸的人很可能是被吓坏了。他们是否试图救助文森特也不得而知,但显然在匆忙冲入无尽暮色中之前,他们还有时间且足够镇定地收走了那把手枪以及梵高所有随身物品。从梵高受伤那天起,雷内和他哥哥再也没有出现在奥威尔镇。
任何自杀都本应包含个人的动机和单独的行动,既然如此,为什么梵高还要竭力主动声称这件事是他一人所为?为什么他力劝警官不要因枪击“指控任何人”,并坚持独自承担所有责任? 梵高的辩解表明了他的决心,他想保护萨克里顿兄弟,不让他们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牵连。可为什么明明他是一场可怕事故的受害者,却还反复“坦白”说是自己想自杀才开了枪?
传记作者史蒂文·奈非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倾向认为,除了保护萨克里顿兄弟,还“因为文森特渴望死亡”。正如梵高曾写过的一句话:“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不论是意外、疏忽,还是恶意所为,雷内可能带给了梵高期待已久却不愿或不能自己实施的解脱,梵高终其一生都将自杀贬作“道德上的懦夫行
为”、“不诚实的人的行为”。在结束了此前糟糕透顶的巴黎探访后,梵高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给弟弟提奥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负担,他觉得“抽身离开”的机会到了。既然达到了死亡目的,再将萨克里顿兄弟拉进来接受质问和忍受羞辱就没有必要了。
“自杀说”符合世人对艺术家传奇的戏剧化想象
就在梵高返回拉乌尔旅店之后的数小时内,关于他如何受重伤的各种流言满天飞。这些小道消息迅速地整合成为了一个情节跌宕、要素齐备的戏剧化故事,描述了在7月27日所发生的状况。而这个故事被几乎所有后来的记述所采用———“梵高从他所住旅店的老板拉乌那里借了把左轮手枪,并在那天下午他通常外出作画的时候带上了这把手枪。随后,他爬上河岸,步行了一段路程后,来到位于镇外上方的那片麦田。就在这片麦田里,他放下所带画具,开枪自杀。这一枪未能致死,子弹没有射中心脏,却使他失去了意识。等到他重新苏醒时,夜幕降临,所以他无法找到那把枪。他只好从陡峭的河岸上蹒跚而下,回到拉乌尔旅店去寻求医疗救护。”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看上去似乎都是令人满意的故事。它给一段不可否认的悲剧人生加上了“合适”的悲剧性结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漠视而结束了自己生命。
同样是印象派代表人物,莫奈盛年成名,画也卖得好,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不缺。而梵高生前绝大部分时间里,画卖不掉,也得不到评论界认可,而到他死后,画作反而成了资本的宠儿,卖价后面的零数得人眼花。如此对比下,再加上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梵高越来越具有了通常意义上“为艺术牺牲的气质”。虽然他去世的那一年,其画作已经开始受到瞩目,一份法国报纸把他的成就与伦勃朗和维米尔相提并论,一位比利时艺术家以400法郎买下了他的一张画,但是,艺术给画家带来的超高回报,梵高生前基本上没能享受到。
而在梵高死后的数十年中,他很快声名鹊起,享誉四方,这个故事毋庸置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1934年,作家欧文·斯通据此写出了畅销小说 《渴望生活》,梵高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永久地成为这位艺术家传奇人生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梵高的声誉又上升到了新高度,1953年是他诞辰100周年纪念,3年后由 《渴望生活》 改编而成的同名影片上映,并获得奥斯卡奖项,梵高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的决绝选择演变成了无可辩驳的神话。
可以说,梵高在钟爱的麦田里自杀的一枪,使这个不折不扣的火热浪漫主义者一下升华为艺术的圣徒。人们感慨于梵高生前籍籍无名不被理解,死后名垂青史,把他被奉为献身真理与梦想的标志性图腾。很大程度上,“自杀”使得梵高为艺术献身的先知形象,笼上了完美的光环,更贴合众人的想象。
有评论界声音直率指出,新的 《梵高传》 正好给了大家一次了解客观事实、直面梵高画作的机会,因为一旦对艺术家的幻想消逝了,作品本身的精神往往便自由了。对于艺术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创作过程,那是他个人精神与外部世界和解的方式。对于这个要求和解的动力及所采取手段,外人很难轻易理解,那是无法被第二个人复制的内心世界。然而一旦画面完成,艺术家便不再需要它,他无暇顾及自己做了什么,便要继续起航寻觅创作的新大陆。由此作品独立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毕竟,梵高
这座美术史上的里程碑未竟的事业,已被无数的后继者们拓展。而只有不断地迎来崭新的目光,梵高的那些杰作才能永久地保持活力与生机。
大数据时代,人物传记研究的“地平线”已被改写
难得的是,《梵高传》 并没有“数典忘祖”,它在介绍里说:“尽管关于梵高已有无数著述,他那悲剧人生的模糊面目也已长期流行于大众文化中,但是在过去的70余年里,还没有一部书像《渴望生活》 这样,对这位艺术家的一生做出了如此严肃而又野心勃勃的探索”。在《梵高传》 中文译者、浙江大学教授沈语冰看来,如果说 《渴望生活》 是70余年前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如今,关于梵高的传记,甚至宽泛一点讲,整个梵高研究的地平线,已经被改写。
普利策奖得主史蒂文·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组织了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依托梵高博物馆档案和学术研究,取材数千封书信和海量文献,历时十多年巨细靡遗的工作,写就这本厚重的千页 《梵高传》。这两人可谓是合作默契的老搭档,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也是艺术期刊撰稿人,合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他们带领幕后团队,在写作研究中采用数码技术,发明了特别的软件,交叉研究解析10万张数码卡片组成的数据库。光是为此书所做注释就多达2.8万条,打印稿逾5000页。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专门开设持续更新的网站,深度整合有关梵高的参考文献、文本注释、画作和照片。读者很快就会明白,西方书评人那句“材料的丰富性令人屏息”是多么贴切。
尤其是数据库这块,它将传记写作和艺术史研究带进了数码时代。当代计算机技术对多达10万张卡片所作的数据处理,让这项本来有可能耗时30年的工作,得以在10年内完成。书评人鲍勃·杜甘就评价,这本 《梵高传》 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梵高,“与此书相伴的网站对未来的学者和传记作家来说,既是一种邀约,也是一种挑战。《梵高传》 作为文森特·梵高新的权威传记脱颖而出,也将参与塑造下一代眼中的文森特。”
如果说,前辈传记作者要么还处于与农耕文明相当的个人写作时代,要么只是利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便利,《梵高传》 却是受惠于资讯爆炸的新时代,建立在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大规模的合作之上。除了动用乔·邦格 (提奥的妻子、梵高的弟媳) 亲自翻译的经典 《亲爱的提奥:梵高书信》 外,还有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一项重大出版计划,那就是花了15年才编撰完成的 《文森特·梵高书信全集》,客观完整地呈现了梵高的生平。这部书信全集将于今年4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引进推出。
这一点远不止是研究资料数量上的更新,更是质的变化。由于有了更多旁人的书信作为佐证,这些书信就与梵高本人书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互相交叉、关联、引证,同时也彼此质询、驳诘、映照。业内公认,《梵高传》 对梵高书信本身的性质做出了新颖而独特的阐明。从交互的书信往来中,两位作者发现梵高的书信并非句句真实,里面充斥着夸大、隐瞒、说服,甚至欺骗。在沈语冰看来,这一新的梵高研究著作,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澄清梵高死因本身,当然澄清这一点已经意义非凡,“由于梵高的死关乎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格、他的艺术,关乎已经流行了近百年的浪漫形象,因此尽可能合理地还原历史真实,其意义将是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