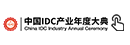自2013年大数据元年以来,国家先后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不但激发了商业繁荣,也向我们作出了美好承诺——市场环境高度透明、搜索成本降低、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准入门槛降低、卖方力量削弱、互联网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最终通往完全竞争之路。
当我们沉浸在市场完全竞争的错觉中,算法经济却反向改变了传统竞争机制,如何实现算法公正成为回应技术革新难以避免的法律问题。算法对传统共谋理论的适用、传统执法工具如何识别、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归责算法共谋等问题提出挑战,驱使现有反垄断法共谋规则向新领域拓展。
值得注意得是,我国算法合谋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引导“算法公正”有必要未雨绸缪。笔者认为,数字市场的良好运行应遵循“竞争优先、慎用管制”理念,并兼以制度与技术保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降低市场价格透明程度。一定的价格透明度能增加消费者福利,过度透明的价格会导致经营者更易调查了解市场定价行为,从而为共谋提供便利。算法合谋中,企业利用算法了解市场竞争者价格并实时跟进,瓦解其他竞争者降价行为福利,“心照不宣”地在透明市场中公然“合谋”。
市场价格高度透明导致企业之间并无协商也能达到明示合谋效果。竞争者之间采取同一非透明性算法和信息交换行为令市场透明度增加,一方面可能提高效率和福利,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反竞争风险。因此执法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增加算法透明度,并将信息交换行为纳入反垄断法制度框架内以降低市场价格透明度。
降低市场价格透明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度披露损害社会福利的定价算法,增加此类算法的透明性,便于全面追踪企业利用此种定价算法的思考及决策过程,并置于执法机关的监管之下,以从根本上破除竞争者主观意思联络。其次,规范竞争者信息交换行为。信息交换行为具有两面性,因此应规范竞争者的信息交换行为。在实践中,市场结构、被交换信息的本质和非公众信息交换行为是分析信息交换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由于算法合谋能扭曲传统合谋原则达到明示合谋效果,使之难以识别辨认,因此企业算法设计与运行的非透明性、合谋行为高技术性与隐蔽性,向竞争执法机关现有的合谋识别机制提出了挑战。目前世界各地已出现了算法合谋案件,如Amazon案(2015)、Uber案(2015)、Eturas案(2016)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执法部门也相继采取应对措施——德国垄断委员会发布《竞争政策:数字市场的挑战》、美国FTC发布《大数据:包容工具抑或排除工具》、OECD也发布《算法与合谋》等报告。
识别算法合谋,建立内部击破和外部监管机制,存在实践上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内部击破机制应结合本土经验,加大宽恕政策的执法范围并建立足够确定透明的政策规定,增加算法合谋处罚力度从而提高自首概率,通过反向博弈制造“囚徒困境”瓦解算法合谋的垄断行为。外部监管方面则有必要建立市场调查机制、举报人奖励制度。一方面通过监督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决定是否采取救济措施,另一方面有效落实举报人奖励制度,鼓励举报并防止滥用举报制度。
三是采用间接证据综合认定。执法者认定合谋的关键在于达成垄断协议,但由于算法合谋不存在主观意图和垄断协议等直接证据——明示协议的缺失,导致竞争执法机关面对具有明示合谋效果的算法合谋却束手无策。基于算法合谋行为自身的隐蔽性,执法机关和法院有必要采取沟通证据和经济证据等间接证据进行整体评估。
提高间接证据的确定性程度,明确所必需的证据数量,是解决竞争执法机构与法院认定一项“垄断协议”是否存在的重要指标。由于间接证据具有更多模糊性,其并不直接描述算法合谋的具体内容,因此适用间接证据过程中应贯彻审慎管制、谦抑管制理念,对证据采纳方面进行适当的必要限制。同时关注算法合谋行为效果的二元性,厘清反垄断规制边界。算法合谋并非必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算法所带来的“数字效率”“技术创新”“社会公共利益”等是衡量算法合谋是否适用豁免制度的关键要素。
四是明确算法合谋责任主体。在算法合谋案件中,算法的作用不断增加,人类因素逐渐减少。算法本身并不违法,但却不足以摒弃反垄断法的关注,竞争执法机构更应该关心这些算法如何被运用,因此厘清“人类”合谋与“机器”合谋的临界点是执法者确定责任主体的终极难题。
但算法合谋并非完全无法由现有反垄断法规制,信使型、轴辐型算法合谋本质上是“默示合谋”这一老问题的新形式,虽能够依据现有法律规制,但依旧存在证据采集等执法工具挑战;预测型、自我学习型合谋则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
在前两类合谋中,算法是人类意志的延伸,算法的使用者应对合谋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在后两类合谋中,算法因素增加,如何确定最终责任主体,应当综合权衡定价算法类型、企业主观意图以及所造成社会损害大小等因素,以决定最终由算法机器人还是由算法程序的设计者、使用者承担,以确保真正的责任主体无法从责任制度中逃逸。
相关阅读: